不知何时起,我常常在喧闹间隙里,突然感到一种莫名沉静。这沉静悄然飘来,无声无息,如薄雾弥漫于眼前,渐渐漫溢开来,然后便无声地吞没了我。心绪倏然凝滞,时间也仿佛停歇了,只留下一种空茫的寂静。此时,心中便不由然生出一片无名的空缺,仿佛某种东西被无声无息地抽走了,却不知其为何物。
那空缺无声地悬挂着,轮廓并不清晰,如一个未完成的几何结构,似圆非圆,似方非方,边缘模糊却执拗地存在。它既非实质的洞,亦非幻想的虚影,而只是沉默地占据着某个位置——位置何在,我亦无法指认。它不声不响,只是幽幽地悬在那里,仿佛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,悬而未决地停留在心间,既无答案,亦无答案的线索可寻。我竟不知它何时潜入,何时盘踞,何时已然成为我内部不可移除的坐标。
生活有时如同一个缓缓倾斜的平面,我们身在其上,难以察觉地滑行着。可这空缺却如一枚沉甸甸的砝码,悄然压住倾斜的平面,使我的脚步每每踏在平地上也如履薄冰。它无声无息地啮咬我的日常,像细沙落进齿轮的缝隙,虽微小,却足以让流畅的运转生出难以言说的滞涩。忽然停下脚步,屏住呼吸,世界照旧转动,我却听见了某种不协调的杂音,仿佛齿轮间卡住了一粒看不见的砂子。
有些时刻,我端着凉却的茶盏,茶水在杯中微微晃动,映着窗外模糊的光影,映着墙上流动的光斑。目光无意间触碰到光线流溢处,心中那空缺便骤然显现。那些光斑是跳动的,是游移的,是捉摸不定的,然而我的空缺却像一口深井,不动声色地吸附着所有经过它的光与影。光斑落在空缺之上,便如微尘落入深渊,无声地坠落,连一丝回响也听不见。光亮被吸纳,只留下更深的幽暗。这幽暗并非浓墨重彩,只是薄薄一层,却足以隔绝一切温度,使所有光热在此处冷却、湮灭,仿佛从未存在过。
有时,我在路上行走,街灯的光晕晕染开,如同洇湿的墨迹,笼罩着归家的路人。人们各自奔赴,脚步匆忙,他们脚下拖长的影子相互交错、重叠,然后分离。影子们短暂地相拥,又迅速地割裂,各自奔向截然不同的方向。我竟驻足于这影子的聚散之地,心中那个空缺,此时竟如一个空置的邮筒,寂寥地立在喧嚣的街角,无人知晓它静默的等待。人们向它投去匆匆一瞥,却无人停留,更无人递送。它空着,一直空着,空得如同一个被遗忘的约定,一个被时间蚀刻成齑粉的誓言。
那空缺里,仿佛曾有过某种轻灵如游丝的气息,如风般轻柔地掠过我心弦。那气息并不沉重,却足以在心上留下细微的擦痕,一种既非痛楚亦非欢愉的、奇异的牵扯。它像是低语,又如同叹息,只是微微擦过心弦,留下微不可察的颤动。这风曾带着温度,带着我无法破译的微响,吹拂过心头的荒芜。如今风止息了,只留下这巨大的静默,无声地占据着曾经被拂动的角落,一种失去语言,失去形态的静默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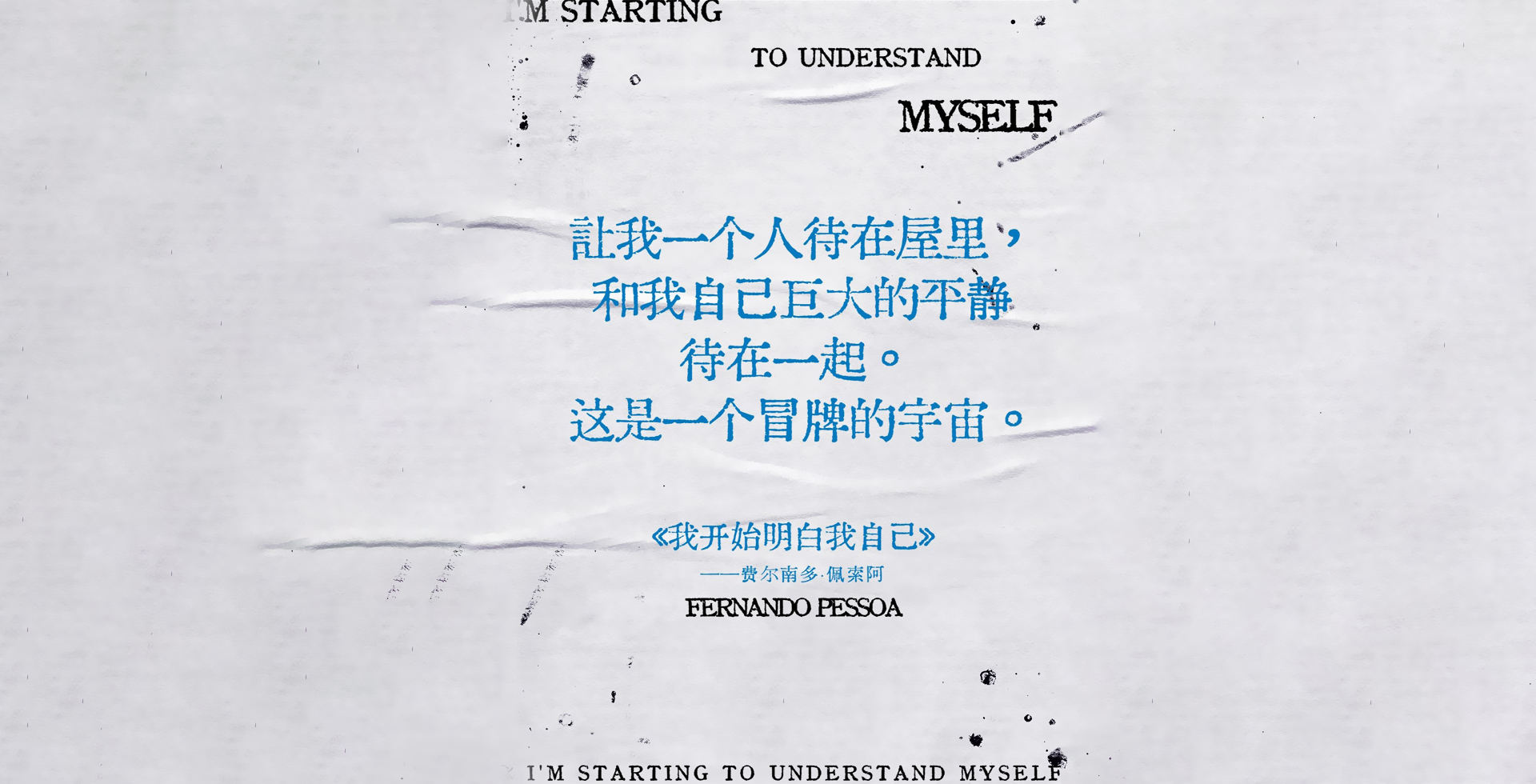
每每夜深人静,白日的喧嚣如潮水般退去,留下沙滩般裸露的寂静。此时,那空缺便愈发清晰起来,在无边的黑暗里凸现。它如同一个无解的方程式,符号冰冷,逻辑缜密,唯独缺少了那个唯一能令等式成立的关键项。我辗转反侧,无法入眠,思绪如丝线,徒劳地想要缠绕住什么,可最终却只缠绕成一片更加混沌的迷雾。空缺依旧悬在那里,没有形状,没有边际,却比任何实物更加沉甸地压迫着胸腔,几乎令我无法呼吸。这悬而未决的几何图形,竟成了我无法回避的星空,每一颗星子都闪烁着谜一样的光。
日子被这沉默的空缺所浸泡,竟像纸张被无形的墨汁渗透了一般,显出微微的异样。生活的纹理悄然改变,它不再是一条顺畅的河流,而像是被无形之物打乱了流向,在平地上也显出微妙的曲折。它不撕裂什么,只是像水一样,不动声色地渗入所有罅隙,使原本的质地发生了难以言喻的变化——如同光线穿过棱镜,无声地折射出异样的光谱。我依然行走,言语,劳作,只是动作间平添了一份不易察觉的迟疑,如同在陌生的水域里跋涉,每一步都带着无声的试探。
这空缺,终究只是我心中一段无名的空白。它不指向任何具体的人与物,不召唤任何清晰的回忆,亦不允诺任何可见的未来。它只是存在着,如同一个始终无法填满的凹陷,一种恒久的缺失感。它并非伤口,没有流血;也非墓碑,无从凭吊。它只是静静地悬在心灵的暗角,像一个没有谜底的谜面,一个没有收信人的地址。
我终其一生,大概都无法知晓这空缺究竟为谁而设,因何而来。它只是如影随形,成了我生命背景中无法驱散的薄雾,一种永恒存在、无法弥补的缺失。也许,思念最深重时,并非具体地想念谁,而是生命本身在时间的长河中刻下的一道深痕——那里曾经有过“在”,如今徒留“空”。
那些无声无息被抽走的,正是我们无法命名,却又在寂静中不断递送出去的——邮筒始终空着,里面堆积着无法投递的晨昏,最终在光阴里化为齑粉。
这空缺,原来正是思念本身那无形无相、无始无终的形态;它并非为了具体之人而存在,它就是我们自身为世界所凿开的一个深洞,静默地承接着一切无法抵达的回音。

